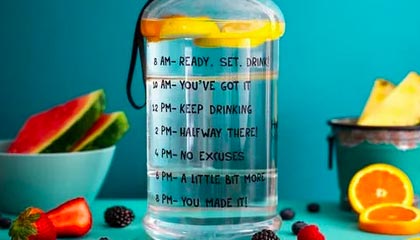糖心vlog封了吗:糖心vlog免费网页版-纪念|巴尔加斯·略萨:写作之为命运
拉美文学巨匠、秘鲁作家、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(Mario Vargas Llosa)于2025年4月13日逝世。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,拉美文学的黄金一代至此落下帷幕,略萨是他们之中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。
略萨的写作人生足以告诉我们,不同于蜇人的,清浊难辨的政治,在一个愈发昏暗的世界上,写作是最小剂量,也最纯粹的英雄主义。1990年,他曾一度进入秘鲁总统决选,但最终落败。从此,秘鲁失去了一位文人总统,却收获了一位不世出的文豪。写作是他的命运,是他体内类似绦虫的存在。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,全部的心智,供养着写作,并以写作的形式,不断地叩问那如污血般涌动在拉丁美洲血管中的横暴的权力。

略萨
文学政治的肃杀中爆炸
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·加莱里诺(Eduardo Galeano)在其出版于1971年的经典之作《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》中哀叹道,自殖民时代起,欧洲资本与美国资本对拉丁美洲的予取予夺,使拉丁美洲沦为“坐在银矿山上的乞丐”。之于这片不断失血的大陆,“我们的失败总是意味着他人的胜利;我们的财富哺育着帝国和当地首领的繁荣,却总是给我们带来贫困。殖民地和新殖民时期的炼金术使黄金变成废铜烂铁,粮食变成毒药。”原来的未来之国,终究还是被历史所绊倒。沉重的,充满殖民所造成的分裂与血腥的过去,如同愈发浓稠的阴影,捆缚它们,使其无法摆脱。
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,则更是一片混乱不堪的,如拼图般破碎的土地。殖民时代留下的国境线,像盘蛇一般啮咬在一起,这里多的是贫弱的小国,一个个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处于下游的失败国家。在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之前,它们就因频繁的内乱而濒临崩溃,甚至陷入军事独裁的高压统治。譬如,1976年1983年间,魏地拉(Jorge Rafael Videla)治下的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在美国默许之下,发动肮脏战争,以绑架、暗杀等手段,弹压异议人士与游击队。8年里,共有约9000至30000名阿根廷公民失踪。皮诺切特(Augusto Pinochet)政变后的智利,同样处于白色恐怖的肃杀之中。
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在晦暗、动荡的政治阴云之外,一如经典现实主义诞生时的19世纪欧洲,市民社会的兴起、大众媒体的发展,为拉美文学的勃发提供了土壤。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全球化,也浅移默化地改变着拉美作家的自我定位。在他们面前涌动的,是整个世界文学的潮涨潮落,而非其母国那几近干涸的文学之流。尽管这一代拉美作家有诸如鲁文·达里奥(Rubén Darío)、豪尔赫·博尔赫斯(Jorge Luis Borges)之类成就卓著的前辈,但更多时候,他们还是从欧洲文学及美国文学的最新进展中汲取养分。在讲述其创作理念的小书《给青年小说家的信》中,略萨不止一次地征引福楼拜(Gustave Flaubert)、福克纳(William Faulkner)等欧美作家的作品。一如米兰·昆德拉(Milan Kundera)所言,直到福楼拜写出《包法利夫人》,小说的艺术才正式超越诗歌的艺术。从某种程度来说,福楼拜是一面镜子,照出后世所有现代小说的可能性。从福楼拜那里,略萨学到了他称之为“连通器法”的写作技法。正如《包法利夫人》中农业博览会一章所呈现的,博览会现场的诸多噪音、官员们的官样文章、农妇的粗糙口语,与罗道耳弗向爱玛·包法利求爱时使用的矫揉造作的华丽辞藻,混合在一起,成为彼此呼应、互相补充的和声,略萨小说中也时常采用与之相似的蒙太奇手法。
福克纳对略萨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。1963年,略萨在西班牙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《城市与狗》,即采用了福克纳式的多线叙事结构。书中不再有湍急且连续的叙事之流,而是有2部8章81个叙事片段。这些叙事片段如同沼泽地里的一个个晶亮的水泊,彼此映照形成这一整片泥泞。如同福克纳的名作《喧哗与骚动》,《城市与狗》的81个片段中,有36个采用阿尔贝托、博阿和“美洲豹”三位角色的第一人称叙事。未尽之处,则由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加以补充。
略萨这部技巧娴熟的初试啼声之作,与卡洛斯·富恩特斯(Carlos Fuentes Macías)的《阿尔特米奥·克罗斯之死》(1962)、胡里奥·科塔萨尔(Julio Cortázar)的《跳房子》(1963)和加西亚·马尔克斯(Gabriel Márquez)的《百年孤独》(1967)一起,将拉美文学带入黄金时代,略萨也由此与另外三部小说的作者并列,成为拉美文学爆炸的四大主将。在出版前一年,《城市与狗》便获得了西班牙Seix Barral出版公司举办的简明图书奖,使略萨成为自该奖于1958年设立以来首位拉丁美洲籍获奖者。小说问世当年,略萨更凭借此书,斩获西班牙文学批评奖及法国的福明托文学奖两项大奖。
略萨小说中的权力与现实
《城市与狗》出版后,很快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,奠定了略萨的国际性声誉。它以略萨青年时代在利马军校中的遭遇为蓝本,描绘了一个畸形且充斥暴力的世界。虽然《城市与狗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,但若将之与略萨写于1990年的回忆录《水中鱼》互相参看,我们便可窥见这部小说的内在肌理。小说中绰号“诗人”的阿尔贝托身上,带有青年略萨的影子,他同样出身中产阶级家庭,同样被父亲强制送入军校,同样在军校中以写作闻名。不同之处在于,小说里的“诗人”在面对严酷现实时选择了逃避,他梦想成为和父亲一样在世俗层面成功的人,离开军校时,他下定决心:“我一定用功读书,当一名优秀的工程师。回国之后,跟爸爸一起工作,也要有一辆高级轿车,一幢带游泳池的住宅。我要和玛尔塞拉结婚,当一个唐璜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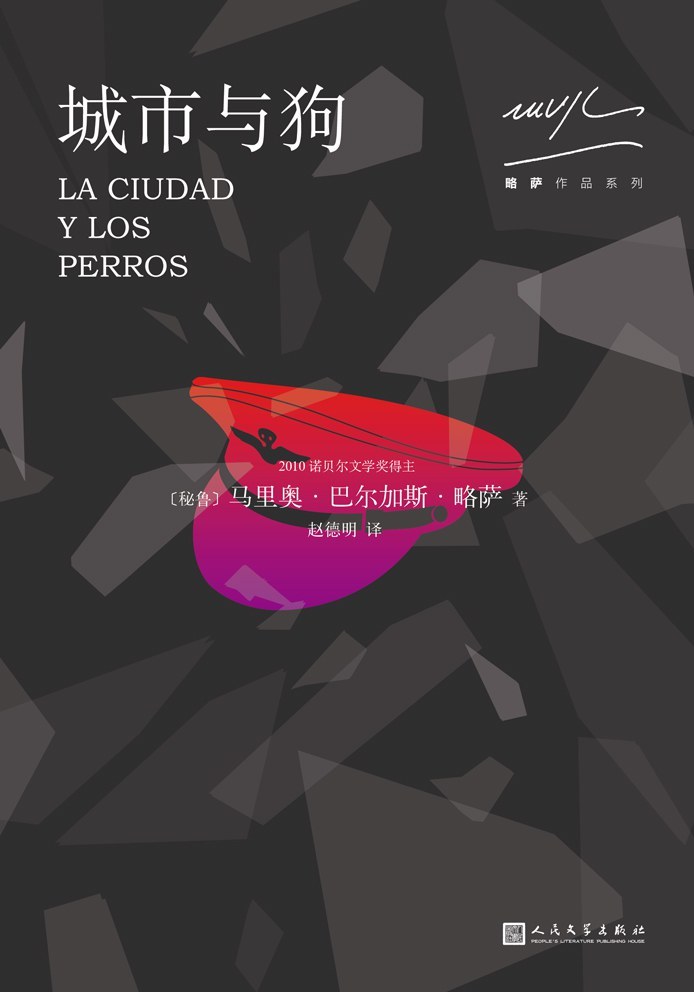
《城市与狗》
之于现实中的作家略萨,《城市与狗》有着特殊的意义,这部书是他向一潭死水的秘鲁社会投下的第一块石头。他等待着回音泛起,而他的写作或多或少能作为对世界的纠正。创作此书时,略萨找到了自己所要书写的对象,即那个横暴的父权制社会,它以暴虐的父亲或专制的军队的形式出现。这一形象同样见于《绿房子》《酒吧长谈》《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》《世界末日之战》等书。在略萨的这些小说中,人对自然、男性对女性、父辈对子辈、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残酷剥削无处不在,并且很大程度上,这些剥削乃是同型异构的。如在他出版于1966年的第二部小说《绿房子》里,印第安人被追猎,鞭打,外来者侮辱他们的妇女,将他们的子女强行带走,送入修道院接受同化教育。被从雨林中强行带入所谓文明社会的印第安首领之女鲍尼法西亚,最终沦为绿房子里的妓女。由是观之,诺奖评委会对略萨作品的点评堪称精准,他们认为,这位秘鲁作家“用制图学般的细致入微描绘了权力结构,并对个人的抵制、反抗和挫败等形象进行了犀利和生动的刻画”。
因此,在略萨的故土,他的小说一度遭到毁禁。秘鲁军政府认为《城市与狗》中伤了秘鲁军队。他们迅速采取行动,在略萨的母校莱昂西奥·普拉多军校,即小说中军校的原型,焚烧了1500本《城市与狗》。嗣后,一众拉美军政府相继封禁了这本书。而即使到了1990年略萨竞选秘鲁总统,并以37%的相对多数票进入决选时,他的政治对手,仍沿袭军政府时期的说法,指责《城市与狗》乃是对秘鲁国家的一次诋毁。
这些企图将小说政治化的人,都囿于大众对小说的流俗看法,他们倾向于认为,小说乃是对现实的忠实拓写,文字惟有以含沙射影的方式,才能发挥效用。在他们眼里,虚构就像现实这块海绵中的水,并不能改变现实的形状,只要将虚构成分榨出,就能百分百地还原小说背后的故事。
诚然,拉美的政治现实是略萨小说乃至诸多拉美小说家的重要母题,如马尔克斯《族长的秋天》(1975)、略萨的《公羊的节日》(2000)甚至直接切入拉美独裁者们的日常生活,及其暴虐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。《族长的秋天》中的族长,乃是一众拉美独裁者的集合体。读者不知道他活了多久,仿佛国家伊始,他就已存在。族长在无尽的纵情声色中滑向腐败的深渊,然而,执掌至高权力的代价,却是他从此陷入无爱的荒漠,背负着沉重的孤独的十字架,直到死亡。《公羊的节日》中则有一个具体历史人物,主宰岛国多米尼加达31年之久的拉斐尔·莱昂尼达斯·特鲁希略·莫里纳(Rafael Leonidas Trujillo Molina)。小说叙述了特鲁希略人生的最后阶段。1961年5月31日夜,他在与情人约会的途中遇刺。特鲁希略戏剧性的死亡引起了作家的兴趣。于是便有了《公羊的节日》这部长篇小说。
在《公羊的节日》中,略萨没有将这位独裁者抽象化为一个暴力符号,而是写出了特鲁希略性格的多重向度。一方面,特鲁希略的上台自有其历史契机。统治初期,他成功地解决了困扰着多米尼加的外患和内乱。为了治理这个国家,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。许多百姓都曾拥护他,支持他,歌颂他,崇拜他,为他为“大救星”、“大恩人”、“新国家之父”。另一方面,他又以高压手段控制社会,让从普通百姓到总统、议长、军高级将领之类的高层,都长期处在特务机构的监视下。由于周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,多米尼加长期陷入物资匮乏的境地,然其家族却用政治手段牟取经济利益,将国营农场及公司低价强行低价收购,再高价卖出。
已至晚境的略萨,对独裁政治的思考愈发老辣,《公羊的节日》着重描述了滋养出独裁的土壤,即那个充斥着阶级格差的社会。对于独裁之下,文化与思想的被钳制、社会公共空间的收缩,底层民众并没有那么敏锐的文化神经去感受。他们所需要的,不过是安定温饱的生活。只要有“面包和马戏”作为调剂,底层民众就会对精神生活的受限缺乏实感,他们就会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,相信高音喇叭里政府的宣传,感念独裁者的恩德,对他突然的死亡如丧考妣。然而那一刻的震惊终究只是暂时的,他们暗无天日的日常一如既往。人们遗忘了独裁者,仿佛他从未出现过一样。
作为行动或作为境遇的小说
不过,即使是《公羊的节日》这样直接讨论独裁政治之内在成因的小说,也不能被视为一部纯粹的政治小说。原因在于,小说家的责任并非传递某种政治思想,而是要透过虚构的形式来提纯历史,使历史真相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。因而,此类小说尤其需要看重书写的伦理,它应该是基于历史可能性的虚构,而非依照作家个人的偏见,或某种市场的需要,随意编排人物。对此,略萨曾在《公羊的节日》首发式上表示:“书中有虚构的人物,也有真实的历史人物。但是在虚构的人物中有许多人物并非是完全虚构的,许多受迫害、受拷打的人物都集中了真实人物的影子。因为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事实已经载入史册,小说绝对不能超出时代确定的界限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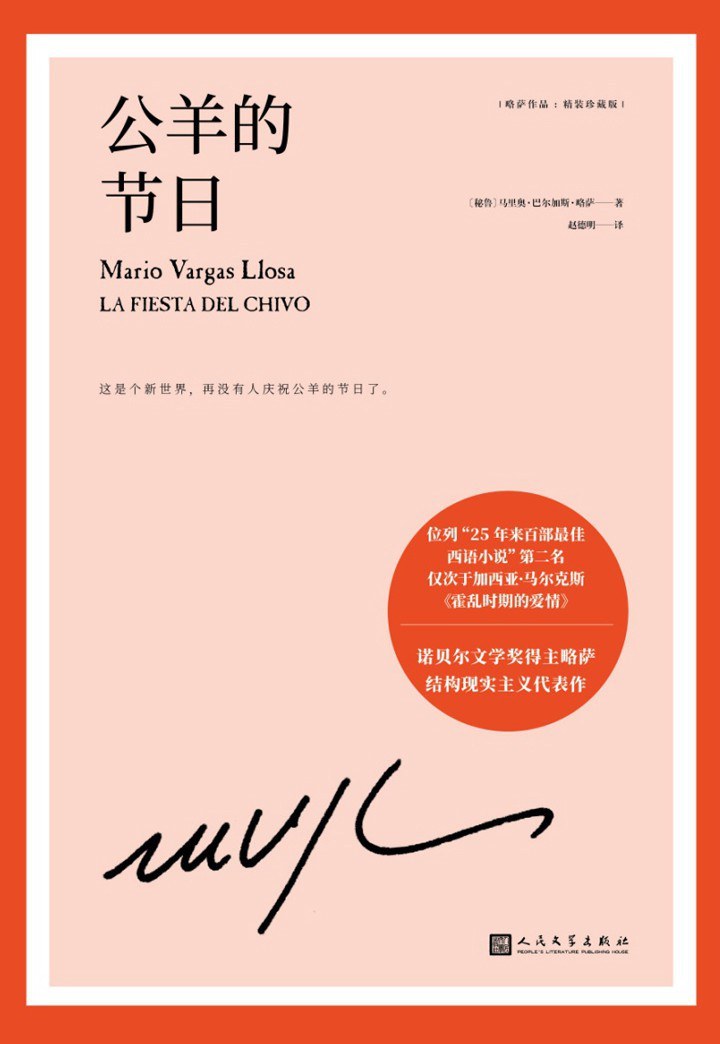
《公羊的节日》
在一个没有故事的时代,写作《公羊的节日》这样一部史诗式的小说是困难的。而略萨的史诗巨作不只有这一部,其于1981年10月在西班牙出版的《世界末日之战》,以同样宏阔的视野,描绘了19世纪末发生在巴西北部腹地农村卡奴杜斯地区的基督教农民起义。这是略萨第一次在小说中描写秘鲁以外的拉美历史。但正是这次尝试,掀开1980年代第二波“拉美文学爆炸”的序幕。
略萨的书写,扩大了现代小说写作的可能性。与之相比,“新小说”由书写人向书写物的革命显得枯燥而贫瘠。略萨的小说证明了,形式实验依然可以服膺于内容。在一流的叙事者手中,文本细密的织体并不会妨害小说母题的钩沉。如果要将他的写作放在小说史的尺度上观察,我们可以援引米兰·昆德拉的说法。在《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》中,昆德拉提到,《十日谈》之类的早期小说,若以如今的眼光看,只是一些简单的通俗故事,然而它们背后却藏着一个与中世纪文学截然不同的信念,这些小说相信,“通过行动,人走出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世界,在这一重复性世界中,人人相似;通过行动,人与他人区分开来,成为个体。”小说在其历史的开端,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一次确证。但到了狄德罗(Denis Diderot)那里,人物开始无法相信行动,他们总是事与愿违,“在行为与他之间产生了一道裂缝。人想通过行动展示自身的形象,可这一形象并不与他相似。”心理小说于焉兴起,人物在外部世界碰壁,转而遁入内部世界的蜗牛壳。在意识流小说中,对内部世界的书写已登峰造极。不过,虽然略萨多多少少继承了意识流小说的遗产,但他更多是沿袭其技巧,而非其世界观。意识流小说总是将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分开,并把心理时间无限拖长。它们终其本质,是关于瞬间的书写,是对时间本身的留恋。
意识流小说所书写的人,是相当原子化的人。略萨的小说同样写人,但他所书写的,不是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,而是作为集体之中的一个关节的人。略萨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某一复杂的关系网之中,如《城市与狗》里的军校、《绿房子》中的妓院、《世界末日之战》里的起义军与政府军。人物的性格特质并不是略萨关心的,他念兹在兹的,乃是人在特定环境之下发生的形变。略萨的小说,由此体现出对权力本质的深刻理解。正如米歇尔·福柯(Michel Foucault)所论述的,权力并非一种能够被某一主体占有的存在,权力是流体,生成于主体与主体间的互动,并随着他们强弱对比的改变而在他们之间流动。可以说,所谓个性鲜明的人物,只存在于经典的巴尔扎克式小说中,而在当代小说中,每个人物都只拥有片段的自我,他们在这个混乱且充满暴力的世界上挣扎求生,并希冀着某种自我完成的可能性。